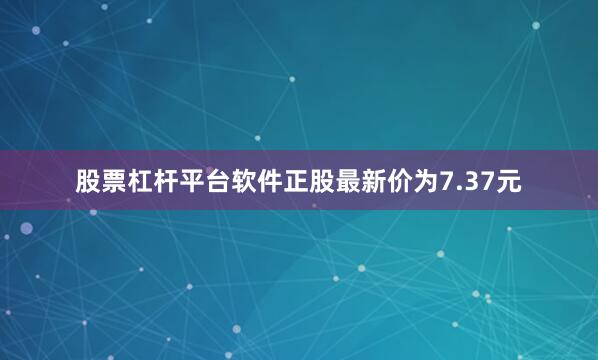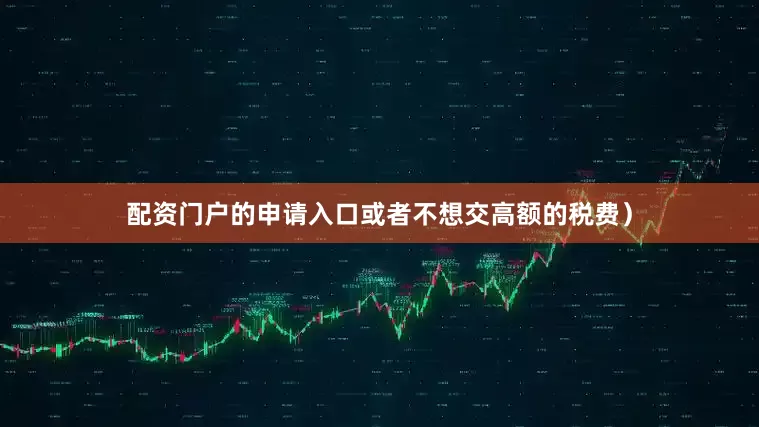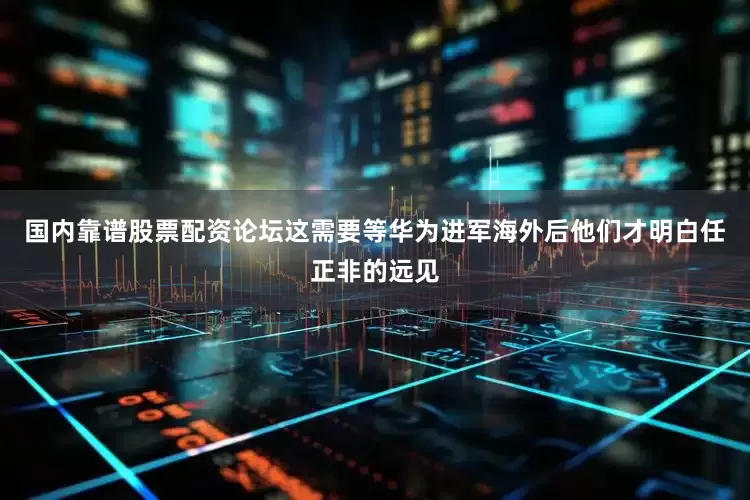"大人!皇上密诏!"信使跪地呈上黄绢诏书。
施琅手一抖,茶杯落地碎裂。他展开诏书,脸色骤变。
"三日内启程进京觐见?"他紧攥诏书,指节泛白。
幕僚李宣忧声道:"大人,听说朝中有人参您擅权自重。"
施琅冷笑:"看来有人要借康熙之手,除掉我这个郑家旧部了。"

01
康熙二十二年秋,福建水师提督府内一片肃静。
施琅将军刚刚收到一纸从紫禁城传来的密诏,要求他三日内启程进京面圣。这份诏书来得突然,没有任何征兆,甚至连例行的嘉奖都没有提及,只有简短的召见命令。
"大人,这份诏书会不会有什么问题?"
李宣是施琅的心腹幕僚,见证了从收复台湾到今日的全过程,此刻他的声音里带着显而易见的忧虑。
施琅将诏书仔细卷好,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
"没有嘉奖,没有理由,只有召见。"他自言自语道,"康熙皇帝不是无的放矢之人。"
"大人收复台湾之功,震动朝野,按理说应当加官进爵才对。"
李宣斟酌着词句,"可是这密诏来得如此匆忙,我担心朝中有人在皇上面前进谗言。"
施琅冷笑一声:"朝中那些勋贵们,哪个不恨我这个'叛将'?从我投靠清廷那日起,他们就没安什么好心。如今我立下大功,想必更有人坐不住了。"
李宣叹息一声:"可不是嘛,都说大人您是郑成功旧部,投靠大清后又亲手收复台湾,打败了旧主的儿子,多少人暗中传您不忠不义。"
"忠义?"
施琅猛地站起身,眼中闪过一丝寒光,"那些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忠义吗?我与郑成功之间的恩怨,岂是他们能妄加评论的!"
李宣见施琅情绪激动,连忙安抚道:"大人息怒,小人只是复述那些流言,并非认同他们的看法。"
施琅摆摆手,走到窗前,望向远处的海面。就是在那片海上,他曾经跟随郑成功南征北战,也是在那片海上,他率领清军击败了郑氏水师,收复了台湾。
"二十年前,我曾是郑氏麾下战将,与他南征北战;如今,我为大清立下汗马功劳,亲手收复了台湾。"
施琅的声音低沉而坚定,"二十年光阴,恩怨情仇,得失成败,尽在其中。若皇上真要问我与郑成功相比如何,我也无惧。"
一旁的李宣听得心惊肉跳,急忙提醒道:"大人慎言!这等话万不可在朝中说出口啊!"
施琅转过身,脸上的表情已恢复平静:"三日之期,我们即刻准备启程。你去准备一份详细的收复台湾战役报告,我要带去呈给皇上。"
李宣领命而去,施琅独自站在窗前,目光遥望东方。台湾已经回归大清版图一年有余,可他心中的波澜却从未平息。
收复台湾的辉煌战果背后,是他与郑成功二十余年的恩怨纠葛,是忠与义、取与舍的艰难抉择。
02
第二日清晨,施琅早早便起身准备行囊。他拿出一个精致的木匣,犹豫片刻后,还是将它放入了随身行李中。那是他多年来的秘密,从未示人。
幕僚李宣敲门进来,手里拿着一摞文书:"大人,收复台湾的战报已经整理好了,请过目。"
施琅接过战报,仔细翻阅。那一仗打得艰险,却也辉煌。康熙二十二年六月,他率领清军水师从澎湖向台湾挺进,一举击溃郑克塽的防守,收复了整个台湾岛。
"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,本将奉旨统领福建水师,出征台湾..."
施琅轻声念着战报开头,眼前浮现出一年前的情景。那时他年近花甲,却依然亲自挂帅出征,决心要完成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。
"大人,当时朝中不是有很多大臣反对您出征吗?"李宣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施琅放下战报,眼中闪过一丝冷意:"是啊,多少人等着看我的笑话。他们说我年事已高,说我与郑氏有旧,说我会徇私......"
"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您与郑成功之间的恩怨!"李宣义愤填膺地说道。
施琅摇摇头:"恩怨?说起来可笑。当年若非郑成功猜忌我、陷害我,我也不会背井离乡,投奔清廷。天下人只知我背叛旧主,却不知我曾几次在生死边缘挣扎。"
李宣神色复杂地看着自己的主人。作为施琅的心腹,他比常人更了解这位将军的过往。施琅原是郑成功的得力战将,曾立下赫赫战功。
然而天启元年,两人因军事策略不合产生嫌隙,郑成功一怒之下差点处死施琅。后来施琅携家逃往福建,投靠了清朝。
"大人当年投靠清廷,也是无奈之举啊。"李宣叹息道。
施琅闻言,目光忽然变得锐利:"不,那不是无奈,而是我的选择。郑成功一心想恢复明朝,却不知天命已改。我选择清廷,是因为我看到了大势所趋。"
"可朝中那些人..."
"由他们说去吧。"
施琅打断了李宣的话,"他们只知郑成功是民族英雄,却不知他有多么刚愎自用。他有勇无谋,最终只能退守台湾,郁郁而终。而我......"
施琅的声音低了下来,"我不过是顺应天命罢了。"
李宣默然。他知道施琅心中的苦楚。作为郑成功的旧部,施琅背负了太多的骂名。然而若非他了解闽南水师、熟悉台湾水道,清廷又怎能如此顺利地收复台湾?
"大人,还有一事。"
李宣欲言又止,"听说朝中有人告密,说您在台湾擅权自重,甚至...甚至有结党自重之嫌。"

施琅猛地拍案而起:"荒谬!我施琅一生为国,岂会有二心?那些宵小之辈,不过是嫉妒我的功劳罢了!"
李宣见施琅动怒,连忙劝解:"大人息怒。皇上圣明,定不会听信这等谗言。"
施琅长出一口气,缓缓坐下:"不错,康熙皇帝英明神武,不是那种听信谗言的昏君。他召我入京,必有深意。"
李宣犹豫片刻,还是说出了心中的忧虑:"大人,此次进京面圣,万一......"
"万一什么?"
"万一皇上真的对您有所怀疑,或者有人借机陷害您,该如何应对?"
施琅沉默良久,才缓缓开口:"李宣,你跟了我多年,可知我为何能在乱世中屹立不倒?"
李宣摇摇头。
"因为我懂得审时度势。"
施琅的声音坚定而有力,
"当年我离开郑成功,不是因为怕死,而是看清了大势。如今台湾已收复,我这把老骨头,早已看淡生死。若皇上信我,我必当竭尽全力为大清效力;若皇上疑我,我也无怨无悔。"
李宣听出了施琅话中的决绝,不禁为之动容:"大人高义!"
施琅摆摆手:"不必多言。继续准备行装,我们明日启程。"
李宣领命而去,施琅独自站在窗前,思绪万千。
二十年前,他与郑成功的决裂;二十年后,他亲手终结了郑氏在台湾的统治。这其中的恩怨情仇,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理解。
03
三日后,施琅的车队已经离开福建,向北京进发。
初秋的天气,道路尚且平坦。施琅坐在马车中,透过车窗望着远处的山水,心中却难以平静。这一路北上,不仅是地理上的跋涉,更是他人生旅程中的重要节点。
他已年过花甲,鬓发斑白。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将领,如今已是两鬓霜白的老将。半生戎马,南征北战,他见证了明清易代的历史变迁,亲历了台湾归附的关键时刻。
"李宣,你说皇上为何突然召我入京?"施琅转头问身旁的心腹。
李宣思索片刻:"大人收复台湾功勋卓著,皇上或许是要亲自嘉奖。"
施琅摇摇头:"若只是嘉奖,大可颁下诏书,何必召我千里迢迢进京?更何况,那诏书上连一个'赏'字都没有。"
李宣低声道:"会不会是...皇上要问您台湾善后之事?"
"有可能。"施琅点点头,"不过,我总觉得此次召见非同寻常。"
行至傍晚,车队在一处驿站停下。施琅独自在房中踱步,挥退了伺候的下人。他从怀中取出一封陈旧的信笺,小心翼翼地展开。
信纸已经泛黄,上面的墨迹依稀可见,却依然透着一股凛然正气。
这是郑成功生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。信中,郑成功指责他背叛大明,投靠满清,是不忠不义之徒。当年读到这封信时,施琅心如刀绞,却已无力回天。
"成功啊成功,你终究不明白我的苦衷。"施琅轻叹一声,将信笺重新收好。
翌日清晨,车队继续北上。途经南京时,施琅特意下车,远远眺望这座曾经的南明都城。当年郑成功曾在此与清军鏖战,一度收复南京,却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。
"若当年郑成功听我劝,不去硬攻南京,或许结局会有不同。"施琅喃喃自语。
李宣在一旁小心地问道:"大人当年就主张不该攻打南京吗?"
施琅点点头:"南京城坚兵精,强攻必然伤亡惨重。我主张应当据守沿海,广集人马,徐图大计。可成功他..."
"他太急于恢复明朝了?"
"是啊,他一心想为父报仇,恢复明室。这份孝心和忠义,我敬佩;但他的急切和固执,却让我不敢苟同。"
施琅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惋惜,"郑成功是条真龙,可惜生不逢时。"
车队再次启程。越往北行,施琅心中的不安就越发强烈。他隐约感到,此次进京面圣,或许会是他仕途生涯中最大的考验。
"大人,前方就是扬州了。"李宣提醒道。
施琅的思绪被拉回现实。扬州,这座繁华的江南城市,在明清易代之际曾经历过血腥的"扬州十日"。施琅不由得想起当年郑成功得知此事时的愤怒与悲痛。
"当年成功得知扬州城破的消息,连夜痛哭,立誓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。"
施琅回忆道,"那一夜,我也在他身旁,见证了他的悲愤。"
李宣沉默不语。他知道,施琅与郑成功之间,不仅有君臣之谊,更有战友之情。这份情谊,让施琅即使在投靠清廷后,依然对郑成功怀有复杂的感情。
继续北上,途经徐州时,施琅再次陷入沉思。徐州是他当年随郑成功北伐时经过的地方,如今故地重游,物是人非。
"李宣,你知道我为何最终选择离开郑成功吗?"施琅突然问道。
李宣谨慎地回答:"听闻是因为郑成功猜忌大人,欲加害于您。"
施琅摇摇头:"那只是表面原因。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,是我看到了大势所趋。满清入主中原已成定局,郑成功却仍沉浸在恢复明朝的幻想中。我劝过他,要审时度势,但他始终不听。"

"所以大人选择了顺应天命?"
"天下大势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"
施琅意味深长地说,"郑成功是条龙,但他逆流而上,最终力竭而亡;而我虽不及他英雄气概,却懂得何时该退,何时该进。"
李宣若有所思:"大人的意思是,成大事者不拘小节?"
施琅笑了笑:"非也。我是说,真正的智者,应当识时务,明大势。郑成功一生戎马,功业赫赫,却因不明大势而功亏一篑。这是他的悲哀,也是我的痛心。"
车队继续前行,一路北上。越靠近北京,施琅心中的不安就越发强烈。他不知道康熙召见他的真实意图,但他知道,无论发生什么,他都会坦然面对。
04
十月初一,施琅一行终于抵达北京城。
"施大人,皇上口谕,请您先在会同馆休息一夜,明日早朝面圣。"一位内侍前来传旨。
施琅躬身行礼:"臣遵旨。"
会同馆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地方重臣的场所。施琅被安排在一间雅致的厢房中,窗外是一片竹林,颇为清幽。
入夜后,施琅独自一人在房中踱步,难以入眠。明日面圣,他该如何应对康熙的盘问?若问及他与郑成功的恩怨,他又该如何解释?
正当他思绪万千之际,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传来。
"谁?"施琅警觉地问道。
"施大人,老奴是御前侍卫统领索额图的家仆,家主有要事相告。"门外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。
施琅谨慎地打开门,见是一位身着灰衣的老者。他环顾四周,确认无人后,低声道:"请进。"
老者进屋后,从怀中取出一封信:"这是家主让我带给大人的。"
施琅接过信,拆开一看,不由得眉头紧锁。信中写道:
"施大人,明日朝会,皇上将问及你与郑成功之事。朝中有人进谗言,称你心怀二意,暗中敬仰郑成功。请大人明日言行谨慎,勿落人口实。"
施琅将信烧毁,对老者道:"替我谢谢索大人,就说我施琅心中有数。"
老者躬身离去,施琅独自站在窗前,望着月光下的竹影,心中五味杂陈。
原来如此,康熙召他入京,是为了郑成功。朝中那些勋贵大臣,果然不肯放过任何诋毁他的机会。
"郑成功啊郑成功,你我恩怨,竟成了他人攻讦我的把柄。"
施琅苦笑一声,目光逐渐变得坚定,"不过,我施琅行事光明磊落,无愧于天地,何惧他人道听途说?"
第二日清晨,施琅早早起身,穿戴整齐,准备入宫面圣。
"大人,您看起来气色很好。"李宣帮施琅整理衣冠,试图缓解紧张气氛。
施琅微微一笑:"生死已看淡,还有什么好紧张的?"
入宫的路上,施琅脑海中不断回想与郑成功相处的点点滴滴。从初次相识,到共同征战,再到决裂分离,最后他亲手终结了郑氏在台湾的统治。这一路走来,恩怨情仇,尽在不言中。
"我与郑成功,到底谁对谁错?"施琅心中默问。这个问题,或许只有历史才能给出公正的评判。
05
紫禁城,太和殿。
金秋十月的阳光透过云层,洒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上。文武百官分列两侧,等候康熙帝的驾临。
施琅站在武将行列的前排,身着官服,腰佩宝剑,神色肃穆。四周不时有大臣投来好奇或审视的目光,但他全然不顾,只是静静等待。
"皇上驾到!"
随着内侍的高声宣告,百官齐声高呼:"万岁万岁万万岁!"
康熙帝一身明黄龙袍,步履稳健地走上御座。虽然年仅二十一岁,但他的眼神中已透露出超越年龄的沉稳与智慧。
"平身。"康熙的声音不大,却充满威严。
百官起身后,康熙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,很快锁定了施琅。
"施琅何在?"
"臣在!"施琅上前一步,躬身行礼。
康熙注视着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将,眼中闪过一丝赞赏:"爱卿此次收复台湾,为朝廷立下大功,朕心甚慰。"
施琅再次行礼:"臣不过尽忠职守,不敢居功。"
朝堂上一片寂静,所有人都在等待康熙接下来的话。这位年轻的皇帝向来心思缜密,做事有章法,召施琅入京必有深意。
康熙沉吟片刻,忽然话锋一转:"朕听闻,郑成功当年颇有才略,曾收复南京,一度威胁朝廷。爱卿曾是郑氏部下,可否详述郑成功其人?"
此言一出,朝堂上顿时议论纷纷。一些大臣交头接耳,眼中满是幸灾乐祸的神色。很显然,康熙此问意有所指。

施琅心中一凛,但面上不露分毫:
"回皇上,郑成功确实才略过人,精通兵法,勇武善战。其父郑芝龙为明朝水师提督,他继承父业,统领东南沿海水师,兵强马壮。"
康熙点点头:"那为何他最终失败,而爱卿却能助朝廷收复台湾?"
朝堂上再次安静下来,所有人都竖起耳朵,等待施琅的回答。这个问题直指施琅与郑成功的恩怨,稍有不慎,就可能落入朝中奸臣的圈套。
施琅深吸一口气,沉声道:
"郑成功虽有才略,却过于刚愎自用,不善审时度势。当年他强攻南京,初战得胜,但清军主力回援后,他寡不敌众,只得退守台湾。而臣虽不及郑成功英勇,却深知天下大势,明白满清入主中原已成定局。"
康熙的眼中闪过一丝赞许:"爱卿此言甚合朕意。然而,朕还有一事不解。"
"请皇上明示。"
"爱卿与郑成功昔日情同手足,为何最终分道扬镳?朕听闻,是因郑成功猜忌爱卿,欲加害于你,是否属实?"
这个问题更加尖锐,直指施琅投靠清廷的原因。朝堂上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。
施琅镇定回答:"回皇上,确有此事。天启元年,臣与郑成功因军事策略不合生嫌隙。郑成功性情刚烈,不容他人违逆,一怒之下欲杀臣。
臣被迫逃离,后投奔大清。然而,臣之所以最终选择大清,并非仅仅因惧怕郑成功,更是因为臣看清了天命所归。"
"哦?"
康熙显出几分兴趣,"爱卿何以见得天命所归?"
施琅坚定地回答:
"大清入主中原,气数已定。郑成功一心想恢复明朝,却不知明已灭,清已立。他逆天而行,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臣虽不及他英勇,却明白顺天者昌,逆天者亡的道理。"
康熙点点头,眼中流露出满意的神色:"爱卿所言极是。那么,爱卿认为,你比郑成功强在何处?"
这个问题如一道惊雷,炸响在大殿之上。
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施琅身上,朝臣们的表情各异。有人幸灾乐祸,有人暗自摇头,更多的人则是屏息凝神,等待这位功勋卓著却又颇具争议的老将如何回答。
施琅站在殿中,只觉一股凉意从脚底直冲脑门。他没想到康熙会如此直白地问出这个问题。
比郑成功强在何处?这不是在考验他的谦逊,而是在试探他的忠诚和政治智慧。
答得太自信,会被视为狂妄自大;答得太谦虚,又会显得虚伪做作。
更何况,郑成功在民间被视为民族英雄,若他贬低郑成功,必然会引起众怒;若他过分称赞郑成功,又会被怀疑心有二意。
康熙端坐龙椅之上,目光如炬,静静等待施琅的回答。年轻的皇帝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,这不仅是一个问题,更是一场考验。
"爱卿何以不答?"康熙的声音虽不高,却在寂静的大殿中格外清晰。
施琅深吸一口气,额头已见汗珠。
他知道,此刻的回答不仅关乎他个人荣辱,更关乎他在历史上的评价。他是叛将还是忠臣?是识时务的智者还是见风使舵的小人?
六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在这一刻凝聚成一个艰难的抉择。施琅的脑海中闪过无数与郑成功相处的画面:并肩作战的日子,争执的场景,最后的决裂...
朝堂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,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。文武百官都在等待,这个答案或将决定施琅的命运。
施琅缓缓抬头,目光坚定地看向康熙,沉声道:"回皇上,臣与郑成功相比..."
话未说完,康熙突然抬手示意他停下。
"且慢!"
康熙的声音陡然提高,"这个问题颇为重要,朕想单独听听爱卿的看法。文武百官暂且退下,留施爱卿一人。"
这一变故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。朝臣们面面相觑,却不敢违抗圣意,只得依次退出大殿。
不多时,宽阔的太和殿内只剩下康熙和施琅两人,外加几名贴身侍卫。
施琅站在殿中,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。他明白,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...
太和殿内一片肃静,只有殿外风吹旗帜的声音隐约可闻。
康熙从龙椅上站起,缓步走下台阶,来到施琅面前。年轻的皇帝身姿挺拔,眼神锐利,周身散发着不容忽视的帝王威严。
"施爱卿,朕再问你一次,"康熙的声音不疾不徐,每个字都清晰可辨,"你认为自己比郑成功强在什么地方?"
施琅深吸一口气,躬身行礼:"皇上,若论武略才识,臣不及郑成功;若论忠肝义胆,臣亦不如郑成功。"
康熙眉头微皱:"爱卿此言何意?难道你认为自己处处不如郑成功?"
施琅抬起头,目光坚定:"然而,臣比郑成功强在一点:臣能识时务,明大势。郑成功虽才华横溢,却因固执己见而失败;臣虽平庸,却能顺应天命,终成大事。"
康熙的眼中闪过一丝赞赏,但脸色依然严肃:"仅此而已吗?"
施琅沉思片刻,继续道:"臣还胜在能屈能伸。郑成功宁折不弯,最终郁郁而终;而臣懂得何时该退,何时该进,因此能为大清立下收复台湾之功。"
康熙点点头,又问道:"那么,在治理方面呢?"
"臣收复台湾后,实行抚绥政策,安抚民心,使台湾百姓归心。而郑成功当年占据台湾,虽也有治理之功,却因过于急切恢复明朝,征调过重,导致民怨四起。"施琅回答得滴水不漏。
康熙沉吟片刻,缓步走到殿内窗前,眺望着远处的宫墙。"施爱卿,朕今日召你入宫,不仅是为了考验你的忠诚,更是想听听你对郑成功其人的真实评价。毕竟,你与他相处多年,比任何人都了解他。"
施琅恭敬地回答:"回皇上,郑成功确实是难得的英雄豪杰。他智勇双全,治军严明,用兵如神。当年若非他一心恢复明朝,执迷不悟,以他的才能,必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"
**"你可曾后悔离开他?"**康熙突然问道,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。
施琅略微沉默,坦然道:"回皇上,臣确实有过彷徨。当年离开郑氏,内心挣扎良久。郑成功待臣不薄,我们并肩作战多年,情同手足。然而,大势所趋,明已不可为。臣选择顺应天命,投奔大清,虽有不得已之处,但臣无怨无悔。"
康熙忽然话锋一转:"爱卿,朕听闻你私下里珍藏郑成功遗物,可有此事?"
施琅心中一震,没想到这件事也被康熙知晓。他犹豫片刻,决定如实相告:"回皇上,确有此事。臣确实保存了郑成功的一封手书和一把佩剑。"
康熙的目光变得锐利:"为何保存?莫非爱卿对旧主仍有眷恋?"
施琅跪下:"皇上明鉴,臣保存这些物品,并非出于眷恋,而是为了警醒自己。郑成功之败,在于不识时务。臣保存其遗物,正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不可重蹈覆辙。"
康熙走近施琅,俯视着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:"那封手书上写了什么?"
施琅面露犹豫之色:"那是郑成功责骂臣背叛的信件,言辞激烈,称臣为不忠不义之徒。"
"既是如此,为何还要珍藏?"康熙追问道。
施琅苦笑一声:"正因如此,臣才要保存。它提醒臣,在世人眼中,臣永远背负着'叛将'的骂名。但臣问心无愧,因为臣选择的是大势,是未来。"
康熙眼中闪过一丝了然,随后问道:"那么,如果当年郑成功不猜忌你,你会一直追随他吗?"
这个问题直指施琅内心最深处的挣扎。他深吸一口气,坦然道:"回皇上,若无那次猜忌,臣或许会随郑成功longer time。但即便如此,臣最终也会选择大清。因为臣深知,逆天而行终将失败,唯有顺应天命,方能成就大业。"
康熙若有所思地点头:"你知道吗?朝中不少大臣认为你这个'叛将'不可重用,甚至有人奏请朕将你革职查办,说你暗中与郑氏余部勾结。"
施琅闻言,面色不变:"皇上圣明,必不会听信这等谗言。臣对大清的忠诚,天地可鉴。"
康熙忽然展颜一笑:"施爱卿,朕向来是赏罚分明之人。你收复台湾,功不可没。那些大臣的奏折,朕已尽数驳回。朕相信,真正的忠臣,不在于出身,而在于其心。"
康熙的眼中闪过一丝满意,又问:"爱卿,朕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若有一日,郑成功的后人再起兵反清,你会如何应对?"
施琅毫不犹豫地回答:"臣必当率军讨伐,绝不姑息!臣已是大清之臣,自当为大清尽忠。昔日之情已成过往,今日之责不可推卸。"

康熙闻言,终于露出了笑容:
"好一个'昔日之情已成过往,今日之责不可推卸'!施爱卿,朕召你入京,正是要亲自了解你与郑成功的恩怨,以及你对大清的忠诚。如今看来,爱卿确实不负朕望。"
施琅松了一口气,再次叩首:"臣惶恐,臣只是做了一个臣子应做之事。"
康熙走回龙椅坐下:"爱卿收复台湾,功不可没。朕已决定,加封你为靖海侯,世袭罔替。"
施琅大喜过望,连连叩首:"臣谢皇上恩典!臣必将竭尽全力,为大清效忠,直至生命最后一刻!"
康熙端起茶盏,慢慢饮了一口:"施爱卿,朕还有一事相问。当年郑成功为何会败走台湾?"
施琅思索片刻:"郑成功兵败南京后,原本打算据守厦门、金门等地,但后来不得不撤退至台湾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便是他的父亲郑芝龙被清廷俘获,且多次写信劝降。郑成功为人至孝,却又刚烈倔强,陷入两难境地,终致精神失常,英年早逝。"
康熙意味深长地说:"一个以孝治天下的朝代,竟让一个孝子陷入如此两难,实在是历史的遗憾。郑成功若能像你一样识时务,或许结局会大不相同。"
施琅默然,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
康熙点点头:"爱卿请起。朕知道,民间对你评价不一。有人称你为'民族罪人',有人骂你'背主求荣'。但在朕看来,你不过是一个明白大势、懂得取舍的智者。历史自有公论,朕不会因流言蜚语而怀疑爱卿的忠诚。"
施琅感激涕零:"皇上圣明!"
康熙继续道:"不过,朕希望爱卿能将收藏的郑成功遗物上交朝廷。非是朕不信任爱卿,而是避免日后他人借此生事。"
施琅毫不犹豫地答应:"臣遵旨。臣早有此意,只是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机会。"
康熙满意地点点头:"好,此事就这么定了。爱卿先回馆舍休息,三日后再来面圣,朕还有治理台湾的要事与你商议。"
施琅领命而去,走出太和殿时,阳光正好,照在他的脸上,温暖而明亮。
六十多年的人生,他经历了太多的风雨。从郑成功的得力战将,到背叛投靠清朝,再到收复台湾、被封为侯爵,他的人生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。
而今天,他终于得到了康熙的完全信任,他的忠诚和智慧得到了最高的认可。然而,在这份喜悦的背后,他的心中依然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感。
回到会同馆,施琅独自一人,从行囊中取出那个精致的木匣。打开匣子,里面是一封泛黄的信笺和一把小巧的佩剑。信是郑成功的手书,剑是郑成功赐予他的信物。
施琅轻轻抚摸着这些遗物,眼中流露出复杂的神色:"成功啊成功,你我之间,到底谁对谁错?你为明朝殉节,我为清廷效力,各有各的道理,各有各的坚持。历史会如何评价我们?这或许只有后人才能给出答案了。"
他小心地将遗物重新放回木匣,准备第二天上交给康熙。这一刻,他忽然感到一种释然。过去的恩怨,就让它随着这些遗物一起封存在历史的长河中吧。
三日后,施琅再次觐见康熙,将郑成功的遗物如数上交。康熙甚是满意,详细询问了台湾的治理情况,并采纳了施琅的多项建议。
离京前的最后一天,施琅站在会同馆的窗前,望着远处的紫禁城,心中感慨万千。
"李宣,你说历史会如何评价我?"他忽然问身旁的心腹。
李宣思索片刻,答道:"大人收复台湾,功勋卓著,自然会名垂青史。"
施琅摇摇头:"我是说,关于我与郑成功的恩怨,后人会如何评说?"
李宣沉默良久,才缓缓道:"这恐怕要看是谁来评价了。在满清看来,大人是忠臣良将;在郑氏后人眼中,大人或许是背主求荣之徒。但在下以为,大人不过是顺应天命,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历史自有公论,不必太过介怀。"
施琅露出一丝苦笑:"顺应天命吗?或许吧。但有时我也在想,如果当年我没有与郑成功决裂,历史会是什么样子?"
"大人何必自扰?"李宣劝道,"过去的事已成定局,不如展望未来。皇上如此信任大人,日后必有更大的作为。"
施琅点点头,不再多言。他明白,历史不会因个人的困惑而改变它的进程。他所能做的,就是在这大时代的洪流中,尽自己所能,留下一些微不足干的涟漪。
回程路上,施琅经过南京时,特意下车,遥望城池。当年郑成功在此与清军血战,一度收复南京,最终却因寡不敌众而败退。如今物是人非,昔日的英雄已成明日黄花,而他这个"叛将"却功成名就,世袭罔替。
"历史何其荒谬,又何其公平。"施琅喃喃自语,眼中满是沧桑。
回到福建后,施琅开始专心治理地方,落实康熙的各项政策。他在台湾推行抚绥政策,减轻百姓负担,鼓励汉人入台垦殖,使台湾很快融入大清版图。
康熙二十五年,六十七岁的施琅在福建病逝。临终前,他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《靖海纪略》一书,详述收复台湾的过程和治理之道,留给后人参考。
关于施琅与郑成功谁是谁非的争论,在他死后仍未停息。有人称他为民族罪人,有人赞他为顺应天命的智者。但无论如何,他收复台湾的功绩,已经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,无法抹去。
或许,正如施琅自己所言:"臣与郑成功,一个逆流而上,一个顺应天命。谁对谁错,天知地知。"
历史不会因个人的好恶而改变它的进程,它只会客观地记录每个人的选择和行动,然后交由后人去评说。而施琅与郑成功的恩怨情仇,也终将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,激起阵阵涟漪,却终将归于平静。
在历史的天平上,没有绝对的对错,只有不同的选择和各自的坚持。无论是为理想殉身的郑成功,还是审时度势的施琅,都只是大时代浪潮中的小小棋子,随波逐流,却也各自精彩。
"比郑成功强在何处?"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。但施琅的选择和坚持,已经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。
而这个回答,将随着时间的流逝,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重新审视和评判,直至永远。
钱龙配资-炒股配资开户技巧-配资安全平台-股票如何加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